界面新聞記者 | 張旭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近期,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蕙蘭未來科技城小學推行的“作業熔斷機制”引發熱議。
此前據都市快報報道,余杭蕙蘭未來科技城小學一教師稱,“我們這學期就執行晚上9點作業熔斷機制,學生晚上9:30以后必須睡覺,低年級學生確保每天9-9.5小時睡眠時間,高年級學生每天達到8.5-9個小時睡眠時間(8:00左右上學)。有一點我們還很驕傲,在確保睡眠的基礎上,我們學校四門學科都在區內遙遙領先。”
2024年1月7日,界面新聞聯系到該校校長俞珺。她表示,因工作繁忙暫無時間接受采訪。
何為作業熔斷機制?作業熔斷機制是在把握作業量的基礎上,為學生設定一個作業時間的上限。一旦學生做作業超過這個時間點,就必須立即停止,且未完成的作業無需第二天補做。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通過縮短作業時間來保障學生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從而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
其實,早在2021年4月,教育部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就寢時間以及嚴控書面作業總量;同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又再次強調,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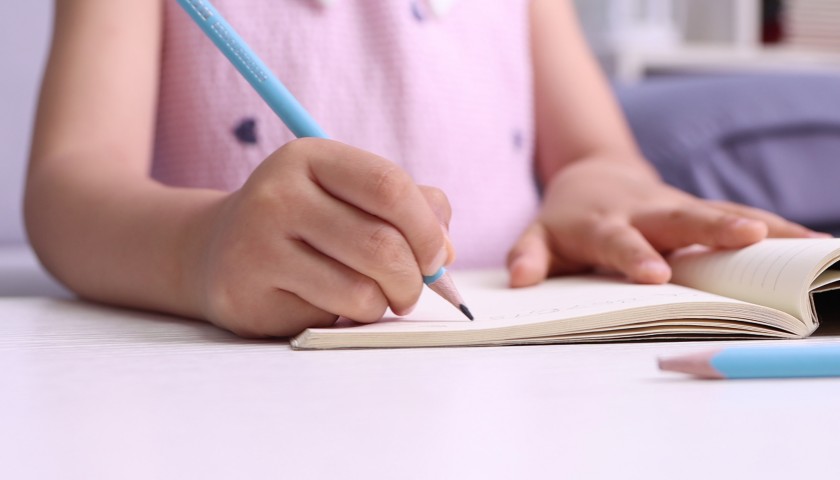
此外,界面新聞注意到,在踐行“雙減”政策的道路上,上述學校的“作業熔斷機制”只是眾多嘗試中的一員,我國已有多個地區的多所學校先后探索并實施了這一機制。
2021年9月,安徽阜陽清河小學實施作業“超時熔斷制度”:作業只要超過晚上9點,或總用時超過60分鐘,必須停止,且不需要補做。此外,江蘇省多所中小學、廣西南寧市桂雅路小學以及江蘇蘇州工業園區的部分學校也相繼推出了類似的作業熔斷制度,旨在為學生作業減負。
作業負擔下,家長與教師間的角力
“陪著孩子寫作業到晚上10點甚至凌晨是多數情況。”一位二胎寶媽劉李林告訴界面新聞,自己常為孩子作業問題感到頭痛。
劉李林是河北人,她的孩子正在上小學二年級。在面對作業這件事情上,她形容自家孩子:“拖延”。
“他本身寫作業很慢,班級其他小朋友可能在課堂上已經完成老師當日布置的作業了,而他每次也得帶個作業‘小尾巴’回家。”目前的劉李林剛生完二胎。月子期間,大兒子的作業完成情況由她看管。
“有時候,我也會覺得老師布置的作業過多了。”劉李林稱,上周六日,老師只布置了兩張試卷。而在這周二,老師布置了兩張試卷外加一份抄寫,還需要我們家長監督背誦,“我認為周一至周五,應該少給孩子們留些作業。”
談及作業熔斷機制,劉李林希望能夠在孩子所在學校推行,進而減少家長和學生負擔,但不免也擔心孩子成績是否會受此影響。
界面新聞注意到,因覺得自家孩子作業繁多,家長投訴老師這一現象屢見不鮮。張然自去年入職以來,已遭遇過三次因作業量問題被家長舉報的情況。
張然是河南人,去年通過招教考試進入廣東省江門市某所公立中學,擔任兩個班級的語文老師。“很難理解,我單科的作業留得非常少了,一共才九道題,而這對于初中生來說,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張然指出,家長在未與自己交流并了解孩子作業具體情況的前提下,僅憑練習冊中三頁的作業量就進行了投訴。“實際情況是,其中的閱讀題占據了大部分篇幅,而孩子在晚托時段并未動筆。”張然的語氣中難掩無奈,“我目前負責的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學,這個階段的學生溝通已屬不易,沒想到與家長的溝通更是難上加難。他們似乎認為舉報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是在發現舉報能快速得到響應后,更頻繁地使用這一方式。”
“原本兩個班級的作業都是統一的,但鑒于該班級家長的行為,我不得不一再減少這個班級的作業量。”張然認為,減少作業量對學生來說并非是好事,需要在減少作業量的同時保證教學質量,“而這無疑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實際上,因家長覺得教師布置作業過多而選擇投訴以及公開在網站留言的事例不在少數。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表示,“投訴的家長各有不同,不排除有的是希望學校少布置,別人少做自己多做。還有一個原因是,學生層次不同,有的學生覺得作業不多,有的卻很晚完成,學校統一布置作業眾口難調,而布置彈性作業,家長也不愿意,認為中高考一張試卷,自己的孩子為什么要做難度低的試卷。其根源還是單一分數標準。”
減負不應從“量”上發力
“減負是個專業問題。”河南鄭州某小學校長王瑜告訴界面新聞,其所在學校并未推行“作業熔斷機制”。“作為一線工作者,我想說,作業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僅僅從量上要求,其實并不完全。”
王瑜指出,要減輕學生的作業負擔,關鍵在于教師的教學方式和作業設計的雙重優化,然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常受限于師資力量的強弱以及整體教育環境的狀況。同時,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還會遇到諸多挑戰與困難。
對此,王瑜強調,首要問題在于學校教學管理的專業性不足,導致作業的設置與指導趨于表面化,僅能側重于數量上的要求,卻忽視了學生完成作業時間的個體差異。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從教育系統的宏觀層面著手,涵蓋教師的專業培訓、考核機制等方面的改進。
“其次,教學工作的深化離不開專業研究。”她進一步指出,一線教育工作者普遍面臨研究時間不足與指導的匱乏,同時,學生學業成績虛實不定且學生評價體系尚未健全。因此,也只能從作業量上為切入點開展減負討論。
王瑜還認為,社會廣泛關注學生的學習時間和作業時間,但對于這些現象背后的教師時間分配、學校時間管理以及學校事務的處理卻鮮有關注。因此,教育質量這一更為核心的問題實際上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視與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界面新聞采訪了多位來自不同省份(包括經濟發達地區)的中小學教師。她們均向界面新聞表示,盡管所在學校并未推行“作業熔斷機制”,但都會對學生的作業安排進行合理考量。同時,她們也提到,大部分學生都會參加校外輔導班。
湖南省長沙市某二年級小學老師蘇鑫告訴界面新聞,雙減政策實施以來,在合理情況下,我們還是會想方設法布置一些作業。“原則上,一、二年級不允許布置書面作業,但還是會布置一些,有的是在課堂上完成一半,然后回去再做一些練習。”蘇鑫說。
蘇鑫表示,學校并未正式推行“作業熔斷機制”,但是,如果家長在晚上通過私信反映孩子作業負擔過重,難以完成,那么孩子可以選擇不再繼續做作業。對于年齡較小的學生來說,如果直接規定一個固定的時間點后就不再做作業,他們可能會故意拖延到很晚,然后直接放棄完成作業。
“是否真的造成學生作業負擔加重?需要具體分析每個學生的情況。有些學生動作迅速,在下午五點鐘放學前就能完成所有作業。然而,有些學生動作較慢,可能無法完成。而這些未完成作業的學生放學后,可能還需要參加課外培訓等活動。等他們參加完培訓再開始寫作業,有時甚至會寫到晚上九、十點鐘。”蘇鑫說。
北京市通州區某小學的老師張佳佳也向界面新聞透露,盡管其所在學校并未正式實施“作業熔斷機制”,但會靈活考慮學生的作業完成情況。她解釋道:“如果孩子因身體不適未能完成作業,家長會出具一份情況說明,次日提交給老師。”
張佳佳進一步說明,許多學生其實能在校內完成大部分作業。但也有一些學生會將作業帶回家繼續完成,而學校大部分學生都會有晚上參加校外輔導班的情況,導致時間緊張。她補充道,實際上很少有學生真的無法完成作業,因此現在老師們也傾向于少布置作業,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建立多元評價體系
學生作業負擔加重的根源在于當前尚未構建出多元化的教育評價體系。熊丙奇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雖然加強學生的作業管理和睡眠管理是重要的,但在唯分數、唯升學、唯學歷的評價體系下,學生的學業壓力依然嚴峻。
界面新聞觀察到,盡管近年來我國在提升普職比例及擴大中職畢業生升學途徑方面已取得進展,但在中考階段,眾多家長仍對普職分流持有焦慮情緒。
“而產生這一問題的根因是還未建立起與普通高考平等的職教高考制度, 從而未能為接受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學生提供平等的升學機會。”對此,熊丙奇認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教育評價體系,構建一個多元化的學生評價體系,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成才路徑選擇。
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名譽理事長、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成員楊東平此前也曾公開發言表示,中國需要新的教育哲學,需要實質性的教育制度變革。實行自上而下的頂層制度變革,實行“源頭減負”,而不是僅僅在學校和家長層面做“末端減負”。
“如果沒有頂層的制度改革,考試制度、升學制度、評價制度不改,讓老師和學生去改,這不現實。”楊東平稱,現在的過度教育,是以提前教育和過度操練為主。現在要從源頭上減少課程數、學時數,大幅降低教學難度、考試難度。
“從源頭上減負,還要推行小學的全科教師模式,改善教育生態,改革并適時地取消中考,促進高中教育的均衡發展和多元化。”楊東平表示。
在實際執行層面,熊丙奇也表示,要完善分類考試改革,加快推進普職融通發展。
“具體來看,不但要讓高職院校參與分類高考,還需要推進讓職業本科、應用本科,以及綜合性院校的部分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的專業,也參與分類高考,即擴大采用職教高考的職業院校范圍。此外,把擴大參與招生院校范圍的職教高考向所有普高學生、中職學生平等開放,關注考察學生在高中期間,選擇技職課程的情況以及學生的技能素養。這將有力地推進普職融合,引導普高開設技職課程,并鼓勵學生選擇。”熊丙奇說。
熊丙奇表示,職教高考對學生技能的考察,應實行過程性評價,而不是結果性評價,即關注學生學習技能的過程、體驗,而非進行一次性技能測試。這種技能測試會導致職教高考也出現應試化傾向。
*應文中采訪者要求,所有名字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