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華商韜略
據媒體消息,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黃達,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2月18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相比今天的明星級專家、學者,黃達教授顯得有些默默無聞,但他對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金融的學術與理論貢獻卻是功不可沒。
黃達教授是“中國貨幣理論研究的開拓者”、“中國金融學的奠基人”。2007年,華商韜略出版《華人金融家》時,曾有幸采寫黃達教授,現摘編部分內容,敬表追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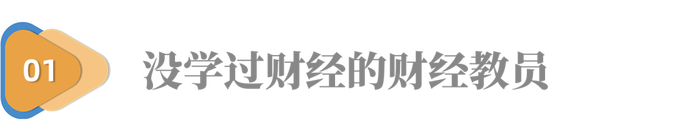
黃達,1925年2月22日生于天津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回憶少時經歷,黃達對自己在天津第一中學的高中學習尤其印象深刻。“這所學校只招男生,入校后一律剃光頭,常被戲稱為‘和尚學校’。學校紀律嚴明,教學堪稱一流。”
在那里,黃達遇到了裴學海、楊學涵、王蔭濃等多位頂尖老師,而且興趣廣泛,博覽群書,但高三那年,一場傷寒病疊加戰亂的艱難,使他失去升學的機會,中止了學業。
此后,原本希望像父親一樣學工并且做工程師的黃達,先后在舊政府機關當過小職員,在私人照相館當過幫工,在親戚家寄生“蹭過飯”,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春,才再考入了華北聯合大學政治學院財經系,并且在年底就“晉級”為了政治學院的研究生。
但這個所謂的財經系,學的基本上只有兩樣:一是革命理論、一是參加土改運動,研究生,研究的也不是經濟,而是“邊政建設”(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
因為學的主要是“革命”,自己也是在這個過程中(1946年底)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所以,后來回憶起這段歲月,黃達更愿意將其說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7年,剛剛“晉級”為研究生,22歲的黃達又被再次“晉級”了:被學校分配到校部從事行政工作,先后擔任過班主任、區隊助理等職務。
1950年,經黨中央和政務院批準,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并組建的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成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大學。當年秋天,黃達成為人民大學的第一批教員,被分配進了學校財政系一個專門講授貨幣銀行學科的教研室,它當時有一個長長的名字——貨幣流通與信用教研室。
這下可是要來真的了,而且肩負的是,為新生的共和國建立起屬于自己的財政金融學科體系的使命。沒有真正學過財經,卻要真正教財經,而且是要教專業知識很強的金融學。
雖然沒有教好這個書的把握,但黃達還是沒有過多考慮,就開始了新工作。
“在那摧枯拉朽、地覆天翻的年代,個人的榮辱得失和事業理想都顯得非常的渺小。雖然也想革命成功之后還是學工,但當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之際,分配我從事經濟理論教學,也就欣然接受了這一決定終身職業的安排。”他回憶說。
也是從那時起,黃達再也沒有離開過教學和金融。

后來,黃達常用“土法上馬”來形容自己不懂但卻要教的那段經歷。
如何“土法上馬”,簡單說,就是先用十足的力氣去學習,學會之后再去當老師,用十足的耐心教別人。他說,這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特殊路子,也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行各業都學蘇聯,金融專業教材也是完全照搬,黃達最初也是如此,但他更早開始了對蘇聯理論和中國實際的思辨,對西方經濟與金融的學習和研究,對中國經濟和金融的獨特思考,這也是他能成為一代先驅大師的關鍵。
1955年3月,黃達發表了《社會主義經濟中國貨幣的本質與職能》,并作為研究主力撰寫了《經濟建設初期農村中的貨幣流通》,邁出了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第一步。
1957年,黃達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人民幣是具有內在價值的貨幣商品的符號》一文,跳出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局限,對中國實際經濟工作的貨幣問題進行了探討。
期間,黃達還高壓鍋式地系統了解、學習與研究西方貨幣信用制度,并且作為總纂定稿人,主編了《資本主義國家貨幣流通與信用》一書。
黃達說,這本書的編寫使他收獲很大,因為寫作既是創作的過程,又是學習與吸收的過程。這本書,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由中國人改編的一本金融學科方面的教材,出版即被全國普遍采用,直到改革開放之初,依然是金融專業學生的“啟蒙書”。
1958年,早就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商品貨幣關系存在著共性的黃達,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如果不講共性,社會主義貨幣流通的“個性”也很難講清。
但當時的金融教材都被分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而后者多是反復在講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卻很少講專業共性問題。
黃達于是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完成一件更加了不起的大事:
將《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合并成一門課,并且主要講貨幣銀行領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下所共同的東西。
這就是黃達主編的,新中國第一本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貨幣流通與信用融合起來分析的專著,也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第一本金融教材的——《貨幣信用學(上冊)》。
《貨幣信用學》不但在體例上與蘇式教材體現出很大差別,也在內容上突破了照搬蘇聯講義的桎梏,為新中國的貨幣銀行學的建立起到了關鍵性的奠基作用。
但遺憾的是,受到金融教師同行歡迎的《貨幣信用學》卻沒為當時的黃達帶來好運。
在當時,這樣大膽的理論嘗試,還是被認為犯有混淆兩種社會制度本質區別的政治錯誤。黃達也于1960年秋的一次政治運動中,遭到持續半年的嚴厲批判,其下冊也因此夭折。
但這并未影響黃達對教學和研究的投入。1958年到“文革”前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運動給國民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破壞,更多人開始感受到,國家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無法從馬列經典著作或蘇聯版的經濟理論中找到解決的答案。
黃達因此更加認真地思考起中國經濟及貨幣金融問題,更加認真地反省了教條式地引用馬克思主義和照搬蘇聯模式的弊病,并更加堅定了從現實出發,扎扎實實從事中國貨幣金融問題研究的學術追求方向,致力探索適合中國現實經濟生活的貨幣流通問題。
1962年,黃達結合自己的研究,發表了他在那一時期的代表性文章——《銀行信貸原則與貨幣流通》。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強調要尊重并按客觀規律辦事,一方面對新中國建立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只承認現金是貨幣的貨幣觀點提出了質疑。其結論是:現金量與存款量之和構成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貨幣量,構成與商品流通相對應的統一的貨幣流通。
黃達的這些觀點在后來得到共識并被寫進教科書,但在當時,依然引起了廣泛爭議。
當爭論還在繼續,黃達卻將研究投向了更廣泛的領域,并于1964年寫了《如何看待價格》一文。這篇文章系統地探討了貨幣與價格等關鍵問題,提出了后來成為普遍常識的真知灼見,但很遺憾,這也成了一篇十幾年沒有發表,只在1988年才收入《黃達選集》的文章。
因為,就在他準備再接再厲時,一場大的破壞運動爆發了,黃達開始挨批判、寫檢查、關“牛棚”,被進干校勞動,這對于正處于黃金年齡段的他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
但黃達仍然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和追求真理的信念。
1973年,剛從干校回到北京不久,他就整理出自己用幾年時間嘔心瀝血研究和準備的《舊中國鴉片戰爭以來工農產品比價資料》(手稿),用事實否定了當時流行的“剪刀差已經消除”的論斷,并深度分析和評判了當時中國物價的現狀。
頗有“塞翁失馬”意味的是,那期間,黃達還巧妙地利用當時的“評法批儒”,對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進行了深入和系統的學習與研究,并與其他同志合作編寫了《商君書經濟思想論述選注》和《歷代法家經濟思想選注》。
這些來自于歷史和哲學的豐富知識,讓他的思路變得更加開闊,也對他后來研究中國經濟現實問題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人民大學復校以后,黃達回到了闊別多年的校園和講臺,其教學研究工作也迎來新的春天。
但這條道路依然不是那么平坦。剛剛“復出”,他就惹了一個不小的麻煩。
1979年春天,有關部門在無錫召開了一次以討論按勞分配和價值規律為主的經濟學家研討會。參會的中國人民大學代表,為了多帶幾篇文章上會以壯行色,讓黃達也趕寫一篇。
黃達于是認真寫了一篇題為《談談我們的物價方針兼及通貨膨脹問題》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是:多年來,中國各種商品的生產條件、市場需求、勞動生產率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變化,而各商品的價格卻長期不變,比價很不合理。要使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就必須調整不合理的比價,并允許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
對此文章,有的學者贊成,更多的人則尖銳批評。《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原打算在試刊號刊登,但因通貨膨脹一詞闖了禁區,沒有人敢冒險行事,直到第6期時,才刪除掉“通貨膨脹”字眼,以《試論物價的若干問題》這個羞答答的標題公開發表。
雖然當時提出物價改革觀點頗為超前,且難以被有些人理解和接受,但黃達卻表現了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品格。他也因此被公認為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首次提出價格改革的經濟學家之一,當然,也有人將他稱為是“鼓吹”通貨膨脹的先驅。
多年后,他的這篇文章更是獲得殊榮:于1998年獲得第一屆“薛暮橋價格研究獎”。
通過在物價問題上的“鼓吹”,黃達還被邀請加入中國價格學會擔任常務理事。
中國價格學會第一次召開常務理事會,學會會長發言說:我們這個學會是堅持黨的雙百方針的,我們的物價工作正反兩方面的意見都要聽取……
黃達笑著回憶說:“我當時就是那反面的。”
此間,黃達還得到一個別致的外號。因為他在《談談我們的物價方針兼及通貨膨脹問題》一文里,小心加謹慎地寫過:“中國的物價會隨著經濟的發展徐徐上漲”,后來的一些學術活動中,黃達常常聽到有人小聲地嘀咕:
“噢,‘徐徐上漲’來了。”
此后,黃達又接著寫了一篇專門論述勞動生產率、積累、消費和物價水平相互關系的文章——《積累增長速度和物價水平》。后來,黃達主編《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一書時,也在書中專門設立了“貨幣與價格”的章節,進一步系統深入地闡述了自己的物價思想。
《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由黃達和陳共、侯夢蟾、周升業、韓英杰等合作編寫,是具有教材性質的專著,出版后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好幾屆相關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并先后于1987年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88年獲得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1989年獲得中國財政學會全國優秀理論研究成果榮譽獎。
從1981年開始,黃達先后發表多篇有關綜合平衡問題的文章:如《綜合平衡和貨幣流通》,《什么是信用膨脹、它是怎樣引起的》(與周升業合作),《財政收支與信貸收支相互配合中的接合部問題》(與韓英杰合作)、《中國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和通貨物價控制問題》等。其中,后者還榮獲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的1984年度論文獎。
1983年,黃達結合有關綜合平衡問題的研究論述,編寫了《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一書。該書集他多年從事中國貨幣金融問題研究之大成于一體,被認為是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理論體系,并長期在中國貨幣金融思想史上占據著指導性位置。
這本書,也是讓黃達日后被公認為一代泰斗和宗師的核心原因。
一個有趣的事情是,因為書中的分析模式與西方的IS—LM模型有相似之處,一位香港人士看了黃達的《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后,誤以為他曾留學英美專門深造金融學。
黃達笑著對他說,我哪也沒去過,學的東西是從蘇聯傳過來的,但也沒去過蘇聯。對方問,他為何能有西方的理論知識背景,他回答說:“只要存在著同樣的經濟活動,并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認真思考,就能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事實上,這是黃達的謙虛,他對西方學說卻是孜孜不倦。他的博士生弟子之一,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南開大學校長陳雨露就曾回憶說:
“英文版的凱恩斯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語言晦澀難懂,鮮有人能通讀該書原文,查閱人大圖書館的英文版《通論》,扉頁上插著一張發黃的借書記錄,寥落的幾個姓名里赫然有著黃達的簽名。”

《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寫作后期,黃達被任命為人民大學副校長,但行政事務的增加,沒有影響他在金融學的世界里繼續探索,只要稍有空閑,他就會繼續教學和研究。
“每年我都給袁(寶華)校長打一份報告,說已經干了一年了,不想干了。可袁校長說,再過一段時間,我也不干了,咱倆共進退。只好再干下去了。”黃達說。
即便實在公務太多,文章不寫了,教學和研究也沒放下來。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但國內金融院系所使用的金融教材卻不能適應這種新的形勢。編出一套既在內容上與時俱進,又能適合中國實際的教材,就成為金融學界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直將金融學科建設視為重點的黃達,于是推動人民大學財政金融系,接受了當時國家教委關于財經專業十門核心課程中的貨幣銀行學教材的編寫任務,并親任主編,會同周升業、沈偉基、王松奇、李焰四人一起,肩負起了編寫更先進金融學教材的使命。即便1991年底,年近67歲的黃達被任命為人民大學校長,教材的編寫仍被他視為重中之重。
1992年,這本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先進的金融學教材——《貨幣銀行學》終于誕生了,并被指定為“國家教委審定高等學校財經類核心課程教材”,迅即推廣至全國,成為全國高校財經類學科的經典教材。
出版《貨幣銀行學》期間,黃達還主編了他所主持的國家“七五”重點課題《貨幣供求量問題研究》的成果——《貨幣供求問題研究系列專著》。
1994年年底,黃達從人民大學校長的職務上退了下來,但他并沒有去頤養天年,而是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了他鐘愛的金融教學和研究上。
1995年,黃達出任了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并作為主編之一,指導和參與了大型工具辭書《中華金融辭庫》的編纂;1997年,他撰寫出版了《宏觀調控與貨幣供給》一書。
他在《宏觀調控與貨幣供給》中強調,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不可割裂,概括地說都是發展的問題,而發展的焦點則是速度問題,發展必須保持一定的速度。
他說,講速度,絕不單純是主觀的愿望,而是生活本身所提出的客觀要求。沒有必要的速度,難以堅定改革的信心;沒有保持一定速度的經濟發展,穩定也就不具備牢固的基礎。
《宏觀調控與貨幣供給》寫作、出版期間,黃達還分別于1999年和2000年,對《貨幣銀行學》作了修訂,并最終完成一個新的重大課題:歷時3年,帶領同事們將《貨幣銀行學》升級為《金融學》,為21世紀初的中國金融學學科建設再次貢獻了一本經典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到《金融學》出版時,黃達已是81歲的高齡了。
很多人可能認為,他這個主編是掛個虛名。但事實卻遠非如此。黃達當主編有個很大的特點,他要求參與編寫的人提供素材,但用還是不用,怎么刪改,最后由他親自決定。
因此,他編的教材里總是既有集體的實踐和總結,又有很多他個人的思想、科研成果。為此,曾有人開玩笑說,別人的書可以抄,但黃達的書不能抄,他的書里都是他自己的真知灼見,行文語氣都是他特有的風格,一抄就看出來了。
除了發表專著,編寫教材之外,黃達還出版有《黃達選集》,以及約400萬字的《黃達書集》,直到2010年,他還出版了《與貨幣銀行學結緣六十年》。
但在總結自己一生的教育研究與學術成果之時,著作等身、位及人大校長的他,卻總是謙虛又自豪地表示:只留下四本教材——《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貨幣銀行學》、《金融學》。
這4本教材,從上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之初,影響了幾代人。

黃達說,自己能有所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頗得益于教學。”
他有一套“教學相長”的方法和理念,貫穿終生。
“如果確實真心誠意地想把學生教懂,首先得自己懂。自己懂了遠遠不夠,還要通過文字,特別是要通過口頭表達自己之所懂。所以說,從備課,到編教材,到講授,到主持討論,到組織考核等等,每個環節都是從‘自己懂’向‘使人懂’的轉化。”
幾十年的教育和研究生涯中,不論行政工作或社會活動如何多,黃達始終把不脫離教學第一線作為自己遵守的準則。從走上講堂到走下講堂,他都是在教與學中度過。
先學后教,邊學邊教,教到老學到老。
黃達不贊同過分渲染教學與研究的矛盾。他常說,研究工作務必要打好理論基礎,而教學恰恰是打好基礎的最佳途徑。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自己多付出時間和心血。
他總是告誡學生:“業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毀于隨。”
論及教書育人,黃達可謂是桃李滿天下。他不但在人民大學的講臺上,為國家培育出了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大學校長、以至國家的高級干部等大量高層次經濟金融人才,更通過全國通用金融教材,間接而深刻地影響了新中國成立至今的幾乎所有金融專業的學生。
但作為國內最早的一批博士后導師,黃達的嫡傳弟子卻不多。
這主要源于他對教育的嚴謹態度,他知道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有限,帶不了那么多的學生,所以干脆不帶,他說:“招人而不育人與一個老師的責任不符”。
想成為黃達門下弟子的人不在少數,其中包括不少官員和商界名人,但他都是婉言謝絕。理由也是,“他們是沒有時間認真做研究的,能不能寫出論文來還要打個問號,他們需要的是一個頭銜,但這與我的想法并不一致”。
他知道這樣可能把一些確實想提高專業水平的人拒之門外,但他還是堅持。
黃達不僅是學術上的導師,更是道德上的楷模。其治學的嚴謹和誠實,為人的真誠與熱情,一直是學界的榜樣。1999年,黃達出版了《黃達文集》,讓人意外的是,他特意把大躍進時期所寫的被自己稱為是“滿是囈語”的文章也一并收錄進來,自揭其短。
他說,這樣“可以自警,也可以使沒有這類經歷的人對于那種歲月的思想紊亂多少獲得點形象的概念”。
《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一書是他受侯夢蟾、周升業兩位先生的一篇論文啟發,進而深入思考研究寫成的。為此,他特地在著作中提到兩位先生的文章,并將其附于專著之后。
他經常告誡他的弟子們,做人要端正,切忌做“墻頭草”,不要為獲一時之利留下終生遺憾。
在金融已經成為顯學中的顯學時,作為知名金融學家的黃達,不斷接到慕名請他擔任顧問或董事的邀請,但他統統拒絕了這樣的“變現機會”。
他還有個“三不”原則:不兼職、不寫序、不寫推薦信。“寫序,自然要寫好話,只簽名呢自己又覺得不妥,真要自己寫還要花時間認真讀這本書,我又沒那么多時間。”他說。
而且,黃達還有一個“堅持自己干,不依賴他人”的習慣。
他寫東西不用人代勞,出門在外也不愿意屬下或工作人員幫忙提行李。
黃達不認為真正的學者能夠不受環境與時代的影響,但他也絕不相信一名“賈桂”式的學者能安身立命。愛好京劇的他,對京劇《法門寺》中小太監賈桂的奴才思想印象深刻,他提倡做學問應當獨立思考,實事求是。
黃達一直謙虛地稱自己為“教書匠”,而且的確不像一些專家學者那樣具有相當高的社會知名度,但事實上,他在學術研究、教書育人之外同樣卓有建樹。
他不但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還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和財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第一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第四屆、第五屆委員、中國金融學會會長等職務,還經常作為各屆政府決策部門征詢意見的學者,在國家現實經濟生活方面發揮、貢獻了智慧。
自稱“哪里也沒去過”的黃達,還十分具有國際化視野和遠見能力。
1983年出任人民大學副校長期間,他就前瞻性地提出:“我們要將學生造就成能夠在東西方兩個文化平臺上自由往返的人才。”并且十分強調大學校園的國際性對推進世界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身體力行地推進人民大學與世界各國大學的交往。
他說:“人類的智慧、學識和文明,永遠是超越國界的……要建立真正的現代化大學,必須實現校園的國際化。”
*華商韜略出品丨ID:hstl8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