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日本是一個結婚率迅速下降的國家,并一直為少子化所困擾。《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稱,日本國民已經開始摒棄婚姻,日本媒體將這一趨勢稱為“獨身主義綜合征”。而《婚難時代》一書作者筋野茜、尾原佐和子、井上詞子指出,有媒體專門提出“婚難時代”一詞,來記述這個顯著的社會現象——每四名男性就有一名終身未婚,每六名女性就有一名終身未婚。
筋野茜在十年前就關注到了這一現象,隨著時間流逝,日本的婚戀問題并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反而愈發嚴重,五十歲之前沒有結過婚的男女在人口中的占比還在持續上升。人們真的不想結婚嗎?筋野茜看到,雖然有不少人對婚姻喪失興趣,依然有不少男男女女在為結婚掙扎和努力著,他們不停地參與“婚活”——即為了找到結婚對象做的事情,比如提升自己、參加化妝、健身、溝通等方面的課程,積極相親、約會交友等等。
政府、企業、婚介機構……誰在操辦“婚活”
日本政府對單身男女的婚戀問題極其關注,主導了不少婚戀援助項目,包括為單身男女創造相識的機會、舉辦相親活動。筋野茜看到,不論是在都道府縣一級的政府,還是在地方基層政府,“通過此類項目步入婚姻的人遠遠多于我們的預期。”這是因為政府主導的項目會更讓人信賴,費用也比民營婚介機構低。
不過,政府舉辦的相親活動也存在問題。活動者有時會因遭到其他參加者的騷擾或者交往不順利而向主辦方投訴,但更大的問題是基層政府常常募集不到參加者。在筋野茜的一則報道中,某地鎮政府舉辦圣誕節相親派對,只有兩男一女報名,無奈之下,他們只好找來未婚的政府職員當“托兒”,結果,非但活動無人配對成功,拋下女友湊人頭的職員也分手了,盡管他們說是為了工作,但對方無法接受。作者將其歸結于官僚主義,舉辦者沒有考慮到,相親者并不希望別人覺得自己在圣誕節這種情侶歡聚的日子里落單,也沒有考慮到政府職員的私生活。這種拍腦袋舉辦的活動,肯定無法取得好成果。《婚難時代》一書據此認為,用納稅人的錢搞這種項目,不可以有“辦完了事”的心態。

有時候,政府組織的婚活會外包給第三方婚介機構。政府策劃的“相親移居旅行團”活動就是如此,在這樣的相親中,就連“信息該怎么發”都有人手把手指點。筋野茜在采訪中看到,婚戀老師就像學校里的老師那樣,無微不至地輔導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缺乏戀愛經驗者,給出諸如“自己發的字數和表情符號的數量要和對方差不多”等實用建議。
雖然不乏盡職盡責的婚介機構和婚戀老師,社會上的婚活機構水平仍參差不齊,還有一些公司非常可疑。在訪問中,筋野茜看到,有一些婚活培訓班專門瞄準那些對婚姻抱有很高期待、不顧一切代價尋找完美伴侶的人。這類培訓班設計了通過搭訕鍛煉膽量的環節,方式是去購物中心和幾十位女店員搭話。有些機構甚至還用“有機會和賽車寶貝約會”、“AV演員教你怎么吸引女人”等噱頭引導學員再掏腰包,“幾乎等同于詐騙”。
除了這些向急于求成的男性開放的婚活“培訓班”,筋野茜也注意到,面向女性的培訓班更喜歡“玄學”,比如以使用能量石手鏈吸引桃花運、用占卜分析前世今生等,吸引那些病急亂投醫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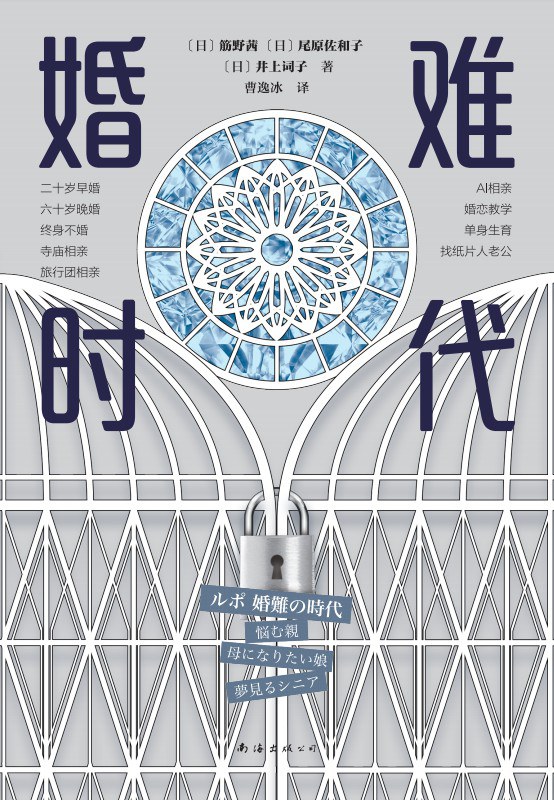
[日] 筋野茜 [日] 尾原佐和子 [日] 井上詞子 著 曹逸冰 譯
新經典文化 | 南海出版公司 2022-10
過去,男男女女在工作中相戀,由上司或者業務伙伴牽線搭橋的情況十分常見,但在今天的日本,這種做法被認為有性騷擾之嫌,并被冠以“婚活騷擾”之名。2016年,為了遏制少子化趨勢、鼓勵支持員工結婚生子的企業,日本政府創立“婚戀導師”制度,鼓勵已婚上司幫助單身下屬走進婚姻,但很多日本人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這是“國家把價值觀強加于人”,是“政府層面的性騷擾”,于是這一計劃政府最終被取消。佐賀縣2017年率先編寫了《婚戀通識讀本》,列出了企業鼓勵員工結婚生子時的諸多注意事項,例如“你沒有男/女朋友嗎?”“你都x歲了”之類的話,或者強邀對方參加相親活動、四處宣揚對方在參加相親活動等,都可能被認定為性騷擾或職權騷擾。
在政府、企業和商業婚介機構之外,一些公益性組織也在操辦“婚活”,比如寺廟。所謂“寺院聯誼”,就是僧侶主持的相親活動。寺院希望可以通過相親活動廣結善緣,加強與年輕人的聯結。而對參與者來說,這種活動與商業相親活動相比報名費不高,在此處參加相親的人對婚姻的態度或許會更加誠懇。
疫情中的艱難相親
隨著新冠疫情在日本的擴散,地方政府的婚姻援助服務和其他婚活都被迫為防疫讓路,一些人因此完全失去了結識異性的機會。2020年5月,東京某婚介服務機構對984名20-39歲的單身男女進行了一次“疫情之下的婚戀現狀”調查,近四成受訪者的結婚意愿因疫情而變強,至于具體原因,選擇“獨自生活感到孤獨、對未來產生擔憂”的受訪者最多,其次是“想找個人一起生活”。
一位化名為“元氣”的41歲男子就是因疫情而產生改變的。他有過二十多個女朋友,一直沒著急結婚,他覺得男人只要有錢,五六十歲也能找到對象。隨著疫情到來,他發現雖然一向自認人緣不錯,但是“假如真遇上緊急情況,我就是孤家寡人”。他由此感到,已經到了該認真選擇人生伴侶的時候,并開始了相親之旅。
身為女性,知惠想要結婚的原因則和經濟狀況有關。疫情極大地沖擊了知惠公司的業務,她上班天數減少,工資也下降了。她很擔憂公司會開除自己,“我很擔心自己能不能一個人過下去,想結婚的念頭也一天比一天強烈。”
在強烈的結婚意愿驅使之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線上相親。在一些相親派對中,男男女女先自我介紹,然后一對一交流,確認互有好感就可以交換聯系方式。井上詞子記錄了一對男女走向婚姻的過程:參加線上相親之后,他們在線上表白,進而虛擬同居——即使是做飯、洗澡也不掛斷視頻電話,最終初次見面就求婚成功,第二天登記結婚。

看來,疫情改變了不少人對婚姻的觀點和婚活的方式,經濟的惡化和生活的動蕩也可能提高人們的結婚意愿。可是,“在人人都不得安穩的時期,越是希望婚姻帶來穩定,結婚的門檻就越高,”井上詞子在《婚難時代》中這樣寫道。
僵化的性別角色仍未改觀
雖然一部分人的結婚意愿因疫情而發生改變,但結婚率走低的根本原因并未改觀。特雷斯特曾經指出,日本社會對異性配偶的排斥與他們性別角色的頑固僵化密切相關。“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掙錢,然而家庭對她們的期望卻沒有改變。日本的工作周適合家有賢妻的男人,工作強度之大讓一個仍需全心照顧家庭的女人無法應付。”

[美] 麗貝卡·特雷斯特 著 賀夢菲 薛軻 譯
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8-05
根據《衛報》報道,日本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日本年輕女性稱她們更愿意單身。《衛報》專欄作家阿比蓋爾·豪沃斯(Abigail Howarth)稱,日本有句古語“婚姻是女人的墳墓”,在今天已被改寫成婚姻是“(女人)來之不易的事業的墳墓”。一名32歲的女性告訴他,“你不得不辭去工作,變成一個沒有獨立經濟收入的家庭婦女。”
井上詞子也有類似的觀察,在今天的日本社會,早婚很可能意味著早育,也幾乎就等同于“放棄事業”,所以女性只能一邊堅守崗位,一邊摸索合適的生育時間。日本社會整體的晚婚化因此也愈發明顯。
“這是對我們社會的一個警示,當兩性角色失衡、女性群體獲得更大的自由而社會又無法適應時,兩性之間的關系就會出現問題。”特雷斯特說。看來,雖然日本政府和相關機構采用各種各樣新鮮的方式組織婚活,雖然疫情產生的不安與孤獨感刺激著人們,但是,如果一些結構性的問題得不到解決,結婚難或許依然是日本社會的一大長久難題。



